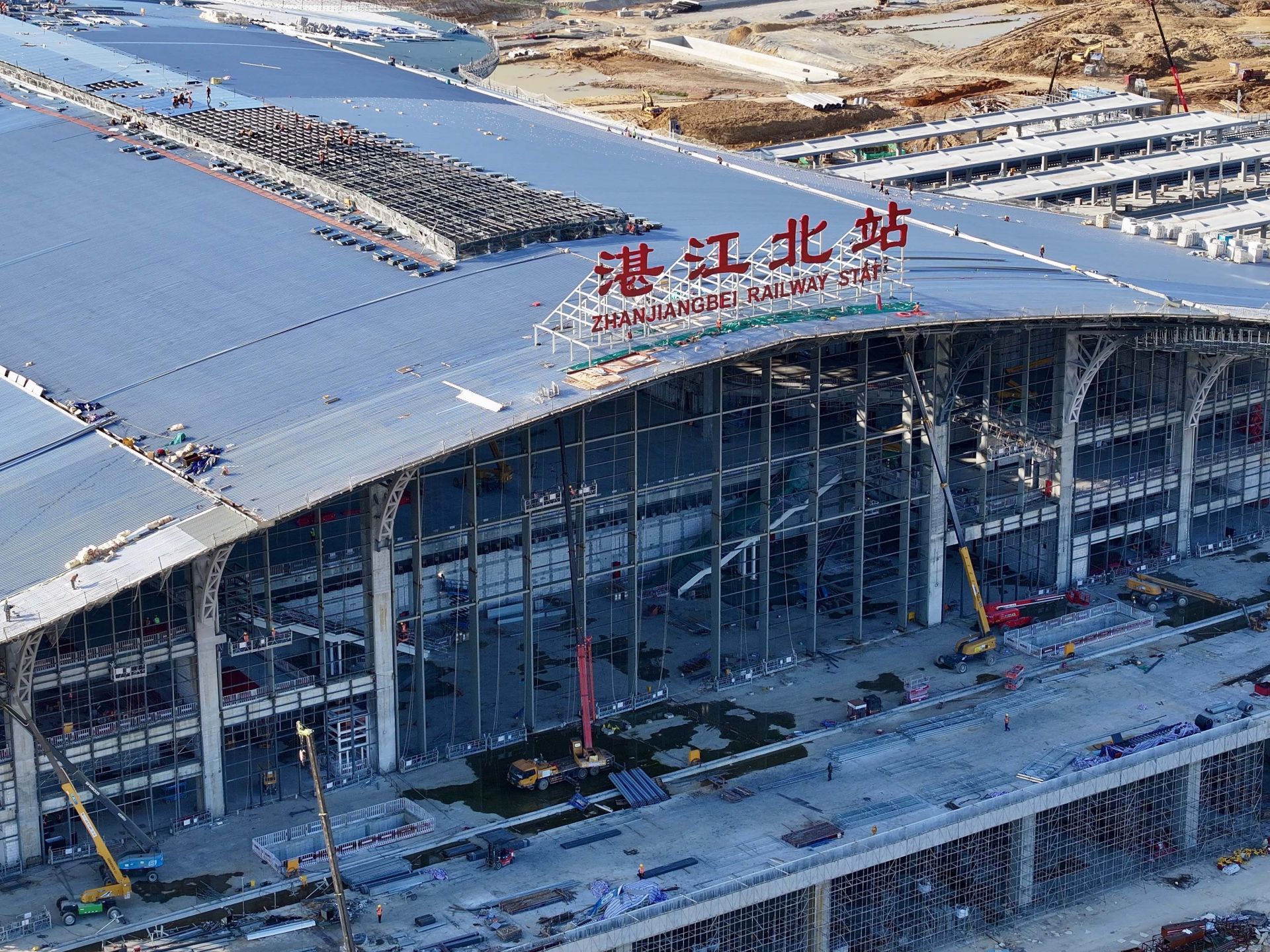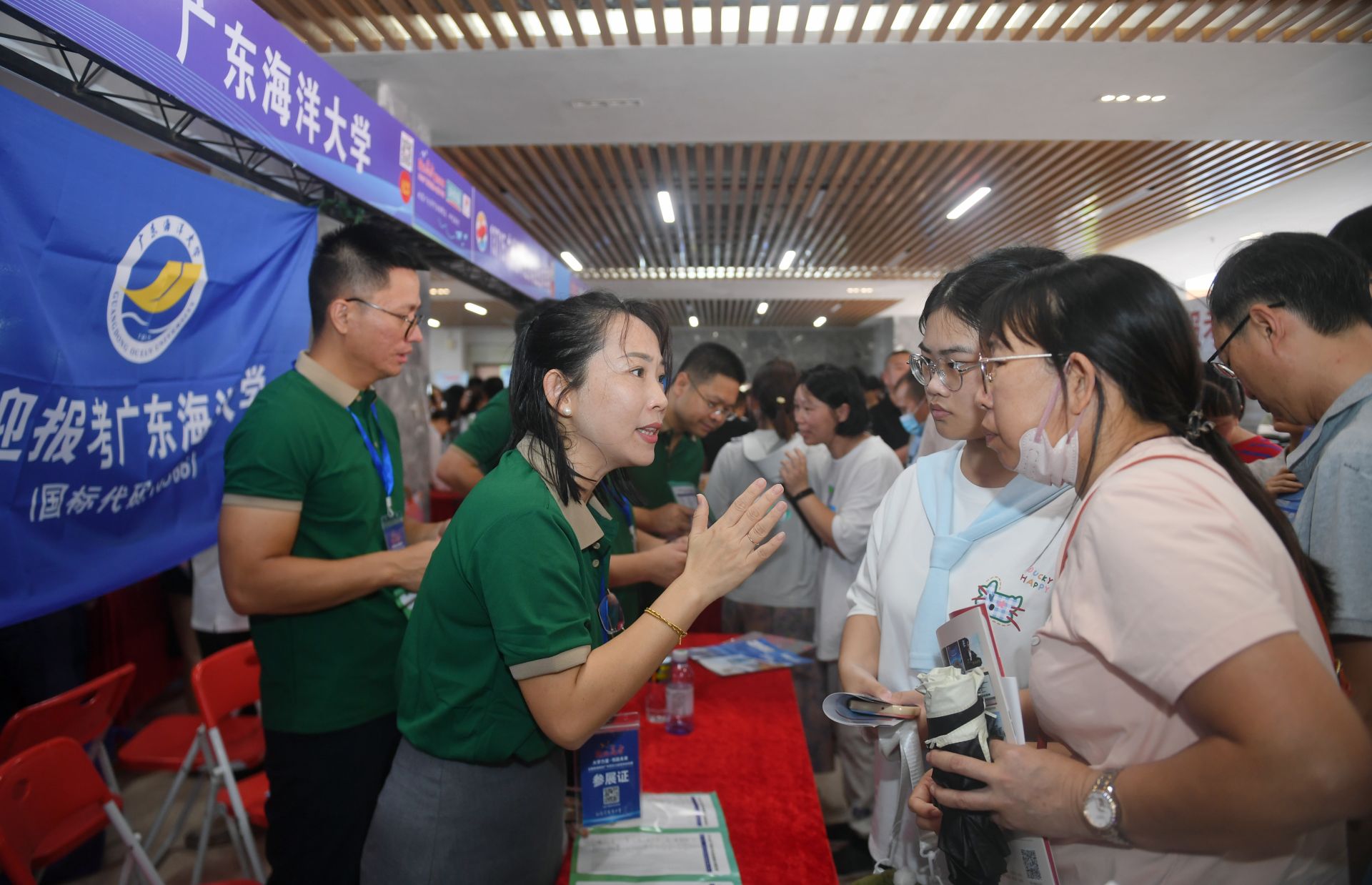父親離開我們已經21年了。這么多年來,我一直想用文字記錄一些父親的往事,可每次提筆淚水總是模糊我的雙眼。又到父親節,我鼓起勇氣,讓記憶的河流緩緩流淌。
父親三十二歲那年,我才來到這個世界。在那個食不果腹的年代,父親本打算一個人過一輩子了,母親卻看中了這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。作為家中長子,我得到了父親全部的寵愛。四歲時的記憶里,父親的身影就是我的整個世界。我小時候很黏他,他去到哪里我都要跟著。他會做木工,就做了一個小板凳綁在自行車的橫梁上,我就可以坐在上面。鄉間的土路崎嶇不平,父親載著我穿行在山澗河畔。上坡時,他推著車,我坐在車上,看到他汗水浸透衣衫;下坡時,風掠過耳畔,我卻從不害怕——有父親在,便是最安穩的港灣。
我上小學的時候經常逃課,父母一大早就下地干農活了,我就把書包藏在廚房的柴草堆里跑去玩了,他們中午回來沒看到我的書包就以為我去上學了。一天,一只母雞跑到柴草堆里下了蛋,該死的母雞下完蛋就會“咯咯咯”地叫,父親去找雞蛋發現了我的書包。父親尋遍村落,最終在溪邊找到正玩得起勁的我,我還是哭鬧著不肯去上學,父親就把我背到學校去,一邊走一邊跟我說一大堆道理……那時候,我覺得父親特別啰嗦。
上初中的時候,有一年冬天,溫度突然下降,我上學忘了穿御寒的衣服。我正在教室聽課,突然門口站著一個人,是父親!他叫了我的乳名:“阿狗,出來拿衣服。”全班哄笑。在那個講究賤名好養活的年代,這個稱呼曾讓我羞憤難當。從那時起,我開始疏遠父親,不想和他說話,覺得他愚鈍,不懂體面。
高中時,我去了縣城讀書,高一時要開家長會。父親風塵仆仆來了,他腳上穿著一雙拖鞋,身上穿的衣服又臟又舊,頭發稀疏凌亂,和平時下田干活一樣。其他同學的父親穿著都是干凈整潔的,父親和他們坐在一起格格不入,顯得又丑又土。家長會后學校安排家長和孩子一起在飯堂吃午飯,父親走在前面,我遠遠地跟在后面,心里五味雜陳。
大學最后一年,父親病倒了,我急忙從學校趕回了家,傍晚母親拉著我出來偷偷地告訴我,父親得了肝癌晚期,醫生說時間已經不多了。我的大腦一片空白,想到我就快沒有父親了,眼淚隨著愧疚和難過不停地流下來。我跑去市里最好的醫院找醫生,求他救救我父親,醫生告訴我:“你父親的癌細胞已全身擴散,已經沒有辦法了,大概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,在家里好好陪陪他吧,如果實在疼得厲害就過來找我拿止痛藥。”接下來的一個多月,我常常往返于醫院和家里,看著曾經健壯的父親現在瘦骨嶙峋在床上蜷縮呻吟,我給他按摩敷藥,疼痛稍緩時,他說:“小時候你那么叛逆,沒想你是個這么孝順的孩子,只可惜爸爸不能享福了。”我轉過身去,淚水又來了。——父親終于還是走了,離開了我們。我雖然很難過,但也覺得父親解脫了,不再受折磨了。
如今,每當生活給我難題,我就會想起父親。他的“笨拙”教會我真誠,他的“土氣”讓我懂得樸實。當我兒子抱怨我啰嗦時,我突然明白:父親從未離開,他活在我的血脈里,我的言行中。就像那輛老自行車,載著愛,在時光里永遠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