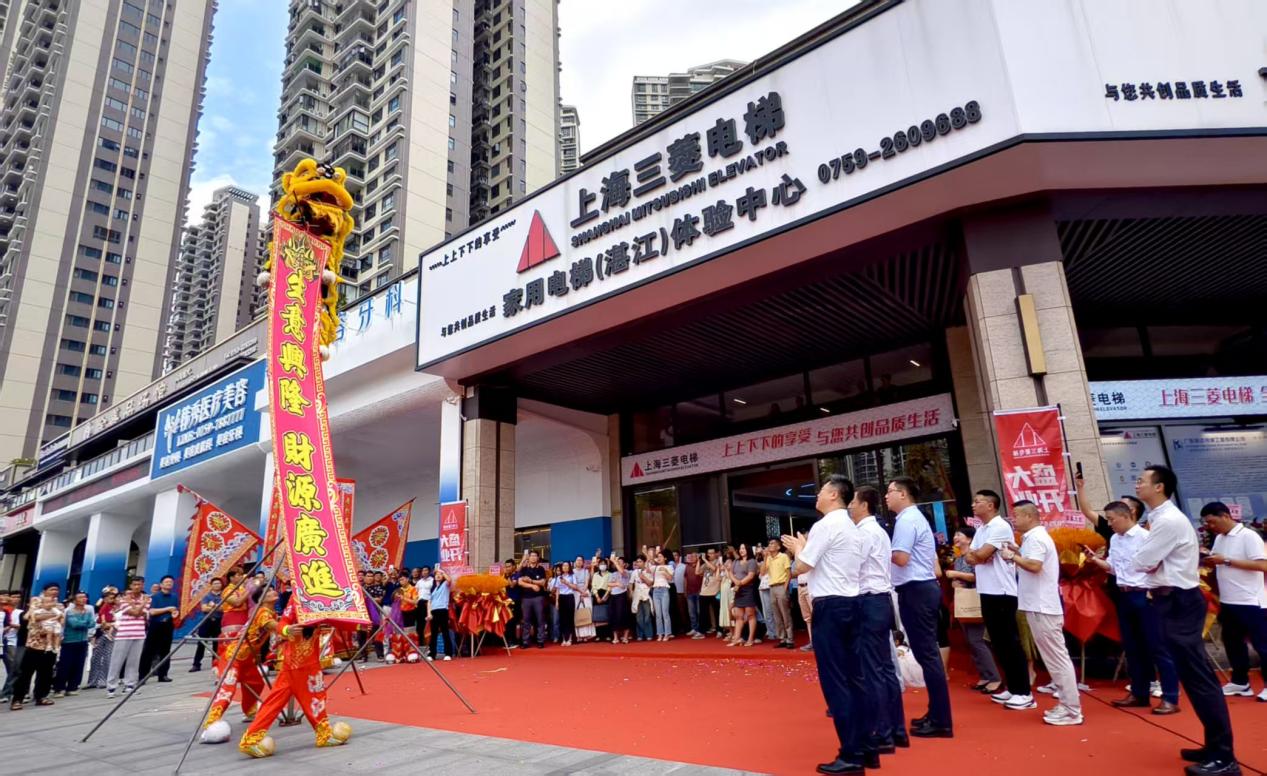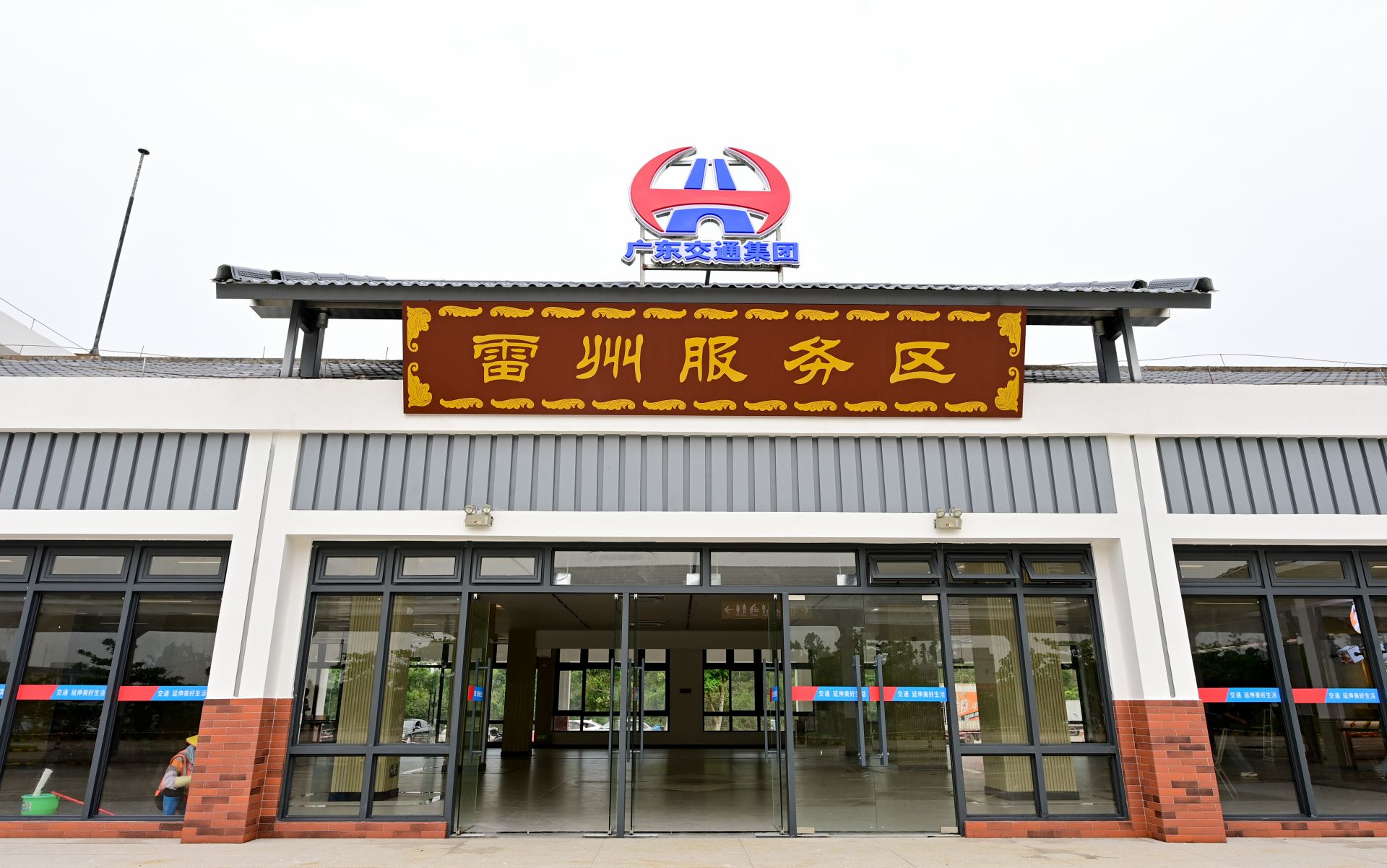萱草花開。陳永鋒攝
萱草花開。陳永鋒攝
千年的時光長河悠悠流淌,宋代的風雅韻味依舊在歲月深處散發(fā)著迷人的光芒。在那動人的詞句間,母愛宛如一泓清泉,潺潺不息,潤澤著每一個游子的心田,編織出一段段動人心弦的故事。
“將母邗溝上,留家白紵陰。月明聞杜宇,南北總關心。”王安石這首《將母》,為我們勾勒出一幅跨越空間的母愛畫卷。邗溝之畔,詩人帶著母親同行,卻無奈將家安置在白紵之陰。月滿中天,杜鵑啼鳴,那聲聲啼叫,恰似母親心底對遠方子女綿延無盡的牽掛。即便南北路途遙遠,母親的心卻始終牢牢系在孩子身上,毫無保留。與恭在《思母》中亦云:“霜殞蘆花淚濕衣,白頭無復倚柴扉”,霜落之時,蘆花紛飛,母親白發(fā)蒼蒼,卻再也無法倚靠柴扉盼兒歸,這份思念化作淚水,浸濕衣衫,同樣是宋代母親對子女深沉的牽掛。遙想宋代的市井街巷,或許有無數(shù)這樣的母親,在如水的月色下,佇立在門前,目光緊緊追隨著子女遠行的方向,滿心祈愿他們平安順遂。這份牽掛,歷經(jīng)歲月的磨礪,在宋韻的時光里愈發(fā)深沉,從未因時光的流逝而褪色。
走進宋代的庭院,萱草花靜靜綻放。“萱草生堂階,游子行天涯。慈親倚堂門,不見萱草花。”萱草,又名忘憂草,于堂階之下繁茂生長,可母親心中對游子的牽掛,又怎能輕易被忘卻?輕柔的南風吹過,拂動萱草的同時,也輕輕撩撥著母親的心弦。她倚靠在堂門旁,目光穿過層層疊疊的山水,望向遠方,心中念著漂泊在外的游子。那風中搖曳的萱草,恰似母親心底無法言說的思念,無休無止。陸游在《游子行》中寫道:“高堂念遠兒,細把平安書”,生動描繪出母親盼兒平安、盼兒書信的急切心情,將母親對子女的牽念融入字里行間。
宋代的母愛,還深藏于對子女的嚴格教導與殷切期望之中。范仲淹在《家訓百字銘》中雖未直抒母愛,但其中“孝道當竭力,忠勇表丹誠”等語句,也暗含著母親言傳身教、培養(yǎng)子女品德的用心。許多宋代母親深知節(jié)儉與品德培養(yǎng)的重要性,她們以身作則,教導子女秉持樸素的生活作風與良好的道德操守。在生活的點滴中,母親們用自己的言行舉止為孩子樹立起做人的標桿。黃庭堅曾言:“盡子職而不我愛兮,終非父母之本心”,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宋代母親對子女道德規(guī)范的重視,期望他們能盡到為人子的責任。無論是日常的待人接物,還是面對困境時的堅韌態(tài)度,母親的一舉一動都深刻影響著子女的成長。
當游子歷經(jīng)漂泊,終于踏上歸家的路途,家中的母親又是怎樣一番模樣?“見面憐清瘦,呼兒問苦辛。”孩子久別歸來,母親的眼中滿是心疼與關切。細細打量孩子,見其面容清瘦,便急忙詢問旅途是否辛苦,身體是否康健。朱弁在《送春》中寫道:“西窗一雨無人見,展盡芭蕉數(shù)尺心”,雖未直接寫母愛,但那舒展的芭蕉葉,恰似母親毫無保留、全然付出的愛。
宋韻里的母愛,在詩詞中被定格,在生活里被延續(xù)。它是臨行前的聲聲叮囑,是深夜里的默默祈禱,是家中永遠為孩子留著的那盞燈火。即便千年已逝,那份深沉、無私的母愛,依然在歲月的長河中熠熠生輝,溫暖著每一個渴望愛的靈魂。在這個快節(jié)奏的時代,我們不妨翻開宋代的詩詞,去感受那份穿越時空的母愛,讓心靈在宋韻的滋養(yǎng)下,被溫柔包裹。